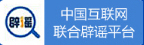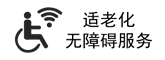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對網絡內容治理的風險挑戰與對策建議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如GPT-4o、DeepSeek-15B等)的技術突破正在重塑網絡內容生態的底層邏輯。內容生產的工業化,AIGC實現了文本、圖像、音視頻的規模化生成,創作效率提升百倍以上。內容形態的多模態融合,Sora等工具可生成高保真虛擬場景,模糊了現實與虛擬的邊界。傳播路徑的指數級擴散,AI生成內容通過CDN加速節點可在數秒內覆蓋全球。這種變革導致網絡內容治理面臨多重困境和挑戰。
一是技術濫用與安全風險升級。生成式AI被惡意利用,導致網絡攻擊的自動化程度和危害性大幅提升。一方面,AI生成虛假信息數量急劇上升。有海外調查機構統計數據稱,2023年5月至12月期間,生成虛假文章的網站數增長1000%以上,內容涉及15種語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據顯示,2024年的AI風險事件總數比2022年增加了約21.8倍,并呈快速增長態勢。另一方面,AI驅動的社會工程攻擊愈發精準高效。攻擊者通過對目標的深度分析,利用AI技術收集大量信息,運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精心生成高度逼真的文件,其中包含精確的個人行程細節,語言風格和格式排版等,成功誘導目標點擊惡意鏈接,此類攻擊的識別難度遠高于傳統釣魚郵件。2024年香港某公司因AI偽造高管視頻會議被詐騙2億港幣,這類內容憑借其高度的逼真性,難以通過傳統審核手段識別,對網絡安全構成了深層次的挑戰。
二是法律責任界定的模糊性。現行法律體系在面對AI生成內容時,難以明確責任歸屬,存在諸多法律空白和爭議。在著作權領域,北京互聯網法院受理的首例AI繪畫侵權案中,四位插畫師指控某平臺使用其作品訓練模型,但現行《著作權法》無法清晰界定AI生成內容的權屬,對于AI在創作過程中的地位和人類貢獻的認定缺乏明確標準。在國際層面,歐盟《人工智能法案》雖將高風險AI系統納入監管,但對“基礎模型”的責任劃分仍存在爭議。中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要求提供者履行內容審核義務,但未明確用戶濫用生成內容的連帶責任,導致執法實踐中“誰違法、誰擔責”的判定困難。此外,《刑法》第 291條“編造虛假信息罪”未涵蓋AI生成的系統性虛假內容,對“利用AI誘導犯罪方法生成”等行為缺乏專項罪名,使得對相關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
三是跨國治理的協同難題。生成式AI的全球化部署引發了多維度的跨國治理協同難題。首先是算法偏見帶來的社會影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指出,主流大語言模型普遍存在性別、種族等偏見,如將高價值職業傾向分配給男性,而女性常被關聯至家務角色,這種偏見通過跨境服務輸出,可能強化全球范圍內的社會不平等。其次,數據流動規則的分裂加劇了治理沖突,歐盟、美國加州和中國等不同國家和地區分別推行了不同的合成內容標識標準,導致企業合規成本攀升,同時惡意行為者可利用監管洼地,通過在法律薄弱地區部署模型并借助CDN加速節點實現內容跨境滲透。2024年某國網軍利用Storm-1516組織制作的虛假選舉視頻在美歐社交媒體的大規模傳播,暴露出跨國取證和執法協作的短板,凸顯了跨國治理協同的困難。
四是倫理失序催生系統性信任危機。AIGC的“幻覺”特性使其可能生成邏輯錯誤或虛構事實,MIT研究顯示,假新聞在社交媒體的傳播速度是真實新聞的6倍,這嚴重影響信息的真實性和可信度。深度偽造技術合成的知名人物語音與影像難以被識別,進一步威脅公眾信任與社會穩定。如2022年一段偽造的烏克蘭總統“呼吁士兵投降”的AI合成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此外,算法決策的不可解釋性,如“黑箱模型”,削弱了公眾對技術的信任,某招聘類AI模型因歷史數據偏差系統性降低女性求職者評分,放大了社會歧視,這些倫理問題的存在導致公眾對生成式AI技術的信任度下降,引發系統性信任危機。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本質是“發展與安全”的平衡。未來,隨著AIGC向通用人工智能(AGI)演進,其內容風險將更加隱蔽和復雜。唯有通過法律、技術、倫理、國際協作的“四維一體”框架,才能實現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健康發展與網絡內容生態的安全穩定。
一是構建動態立法與監管體系。推動高位階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專項立法,明確開發者、平臺、用戶三方在AI生成內容過程中的責任。強制要求對AI生成內容進行標識,規定開發者需公開訓練數據來源(比例不低于30%),平臺建立內容生成日志溯源系統,用戶對惡意生成行為承擔直接責任。修訂《著作權法》,增設“AI生成內容鄰接權”,明確人類在AI創作中的“實質性貢獻”認定標準,解決AI生成內容的權屬問題。在《刑法》中增加“AI技術濫用罪”,將誘導生成犯罪方法、系統性虛假內容傳播等行為納入規制范疇,填補法律空白。實施《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標識條例》,強制要求對AI生成內容添加不可篡改的數字水印(如區塊鏈哈希值),建立“內容DNA”溯源系統,參考阿里云跨境商品監管方案,實現AI生成內容的全鏈路可追溯。推行“算法透明化”制度,要求高風險模型(如醫療、司法領域)公開決策邏輯摘要,提高算法的可解釋性。
二是構建AI對抗AI的技術防御體系。加大技術研發投入,研發“零樣本檢測”技術,如西湖大學的Fast-DetectGPT,基于條件概率曲率分析,檢測準確率達90%,速度提升340倍,突破傳統規則依賴的檢測瓶頸。開發多模態融合檢測模型,如復旦大學的ImBD框架,對修訂文本檢測準確率提升 19.68%,提高對多模態AI生成內容的檢測能力。建立“AI安全沙箱”測試環境,通過紅隊對抗訓練(如OpenAI的 RLHF強化學習)識別模型偏見與毒性輸出,要求關鍵領域模型(如教育、政務)通過第三方倫理安全認證方可上線,確保模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推廣“數字水印+區塊鏈”雙軌溯源技術,確保AI生成內容從生產到傳播的全鏈路可追溯。跟進美國NIST 2025年標準,研發后量子加密算法,構建抗量子攻擊的內容傳輸安全通道,保障內容傳輸的安全性。
三是推動技術價值觀對齊與行業自律。嚴格落實《科技倫理審查辦法(試行)》,要求涉及公共利益的AI應用(如新聞生成、政務服務模型)在部署前通過倫理委員會評估,重點審查數據偏見、決策透明度、社會影響預測等指標,從源頭上確保AI應用符合倫理要求。建立“價值觀對齊”訓練標準,在大模型預訓練階段注入反歧視、反虛假信息的人類價值觀語料,引導AI生成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內容。推動平臺制定“AIGC內容生成公約”,如抖音AI內容聲明機制,建立用戶信用評級體系,對多次生成違規內容的賬號實施算法限流,規范用戶行為。開發“AI內容辨識工具包”,通過公眾教育項目提升用戶對深度偽造、機器生成內容的識別能力,同時建立便捷的公眾舉報渠道,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設置投訴舉報入口,及時處理公眾反饋,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治理格局。
四是構建全球治理共同體。構建多層級協同的全球治理共同體。技術上,研發并應用全球統一的AI內容標識標準與可驗證水印技術,從源頭遏制虛假信息。規則上,依托聯合國協調各國立法,建立數據跨境“負面清單”與風險評估互認機制,統一法律框架。執法上,強化國際刑警組織及區域司法協作,探索電子證據跨境直調通道。同時,推動聯合國框架下“生成式AI全球治理聯盟”落地,制定統一技術檢測與數據流動規則,建立“治理白名單”。搭建“AI犯罪情報共享平臺”,開展聯合執法,實現證據互認。此外,倡導頭部企業公開模型關鍵參數,接受審計,支持中國“公共利益AI平臺”建設,推動醫療、教育等領域開源模型共享。唯有實現技術倫理、法律框架與執行能力的跨國對齊,方能應對生成式AI引發的系統性治理風險。
五是構建前瞻性治理創新機制。引入“監管沙盒”機制,如英國NCSC《安全AI系統開發指南》,允許企業在受控環境中測試新型治理技術,如AI生成內容的實時阻斷算法,通過“觀察-評估-調整”實現監管策略的動態迭代,及時應對新技術帶來的挑戰。建立“技術風險預警清單”,定期評估AGI演進帶來的內容風險,如自主生成惡意代碼、合成現實場景誤導決策等,預留法律與技術規制的升級接口,確保治理體系能夠適應技術的快速發展。支持“計算法學”“科技倫理學”等交叉學科研究,培養兼具技術理解與法律思維的復合型執法人才,為治理工作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撐。建立“生成式AI社會影響實驗室”,模擬極端場景下的內容風險演化路徑,如AI驅動的輿論操縱、認知戰等,提前制定應對預案,提高應對系統性風險的能力。
作者:李如龍;作者單位:四川省委網信辦傳播處